特朗普政府第二次上台後,關稅政策持續升級:將美國與特定國家的商品貿易逆差額,除以該國對美出口總額,所得百分比再折半計算,最終設定10%作為最低稅率門檻。加拿大、墨西哥、歐盟、日本、印度等經濟體,稅率區間達20%至26%,同時取消低價包裹免稅優惠;而對中國的104%的關稅,如「話事啤」下注加碼到125%,145%,245%。美國政府宣稱此舉旨在縮減貿易逆差、重振製造業,甚至解決移民與毒品問題。然而外界普遍質疑,高關稅政策實際推高國內物價、損害消費者權益、擾亂全球供應鏈。香港作為轉口貿易中心與國際金融市場,首當其衝感受到政策波動,這場爭端成為檢驗「經濟安全」理論有效性的現實案例。香港這個高度外向型經濟體,必須清醒認識美國關稅政策的實質意圖。
「經濟安全」異化及其後果
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,其概念興起於冷戰後全球化加速時代。當時各國更關注經濟發展而非安全議題,但隨著國際格局演變,西雅圖WTO會議爆發大規模反全球化示威;亞洲金融危機(1997-1998年)暴露出高度開放經濟體的脆弱性,促使各國重新審視經濟安全內涵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顯示,危機後新興經濟體的外匯儲備佔GDP比重從1996年的8%驟升至2002年的22%。其後,經濟安全逐漸成為涵蓋軍事力量、國際地位和社會穩定的綜合性概念。本質上,經濟安全要求經濟體具備抗外部衝擊能力(如供應鏈斷裂、市場動盪)的同時,保持可持續的全球貿易參與度與發展動能。香港的實踐為此提供了絕佳註腳——即便面對美國的關稅壁壘,仍能依託多元化市場和內地支持快速調整貨流,充分證明真正的經濟安全應植根於開放合作,而非封閉對抗。
然而,當前國際競爭中,「經濟安全」正遭遇嚴重異化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(2024)指出,這種「經濟泛安全化」現象表現為將正常經濟活動過度政治化,導致全球市場割裂。
- 產業回流政治化
美歐日等國以國家安全為名,推動半導體、能源等關鍵產業回流本土或轉移至盟友國家,日本政府甚至不惜提供巨額補貼吸引台積電設廠。根據彭博社統計,2020至2023年間全球晶片產業的政策補貼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,其中高達82%的補貼項目都帶有明顯的「去風險」政治標籤。
(2) 供應鏈意識形態化
與此同時,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(IPEF)和「四方安全對話」(QUAD)等機制,公然將供應鏈按照意識形態劃線,在2023年達成的IPEF供應鏈協議中,有多達14個條款直接針對所謂「非市場經濟體」,試圖構建排除特定國家的平行產業體系。
(3) 技術管制武器化
在技術領域,美日等國聯手構築的「安全壁壘」更顯嚴苛。在人才流動方面,STEM領域的中國留學生簽證受到嚴格限制,參與中國「千人計劃」的學者遭到全面監控;技術出口管制清單被擴大至14大類新興技術;外國投資委員會(CFIUS)的審查案例在五年內激增340%。這些措施已遠超正常技術保護範疇,淪為遏制他國發展的政治工具。
(4) 關稅工具戰略化
更甚者,特朗普政府公然顛覆WTO多邊規則,對價值超過5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。布魯金斯學會研究顯示,這些關稅導致美國企業年均損失160億美元,卻完全未能實現所謂「製造業回流」的政策目標。
這種經濟安全概念的異化已造成深遠危害。世界銀行《全球經濟展望2025》警告,美國關稅政策推高全球貿易成本,影響運輸與物流;麥肯錫《技術趨勢展望2024》指出,貿易壁壘阻礙技術交流,拖慢創新步伐。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夏寶龍主任一針見血地指出:「美國不是要我們的稅,而是要我們的命」,某些勢力的真實目的已完全超越正常商業競爭範疇,演變為赤裸裸的經濟扼殺。
香港經濟的韌性表現
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強調,香港將堅持自由港定位,不跟隨內地對美國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,通過靈活政策吸引資金與人才。儘管面臨關稅風暴,香港經濟展現出較強韌性。數據顯示:美港貿易僅佔香港外貿總額2.91%(出口460億港元,進口2176億港元),遠低於內地貿易規模(4.791萬億港元)。即便美國將香港商品視同內地徵收145%關稅,香港對美出口仍實現13%增長,整體出口增幅達11%,影響相對可控。這得益於香港獨特的經濟結構——服務業佔比超GDP九成,金融、物流、專業服務等核心競爭力並不依賴美國市場。在進口方面,美國貨物僅佔4.3%(內地佔43.5%),電子產品和農產品可從日本、澳洲等地替代;出口方面,61億港元本地產品可轉向內地、東盟、中東等市場(中東市場增長10.6%),407億港元轉口貨物(主要來自內地)可通過新加坡、杜拜等樞紐調整,實際損失僅佔出口總額0.94%。
香港已簽署9份自貿協定(涵蓋21個經濟體)和24份投資協定(涉及33國),積極開拓東盟、中東及「一帶一路」市場。內地14億人口與大灣區8600萬消費者的潛力為香港提供堅實後盾;2025年第一季度香港經濟增長2.5%,當前香港經濟雖保持穩定增長,但美國使全球貿易環境持續惡化,「經濟安全」被異化為貿易武器時,我們又如何破局?
破解「泛安全化」困局
美國關稅風暴將「經濟安全」與「經濟泛安全化」的界線劃得涇渭分明。前者是經濟繁榮的基石,後者則是裹著安全糖衣的自由貿易陷阱。美國高關稅政策表面上是為保護國內產業、減少進口競爭,實則帶來一系列複雜後果。全球貿易體系因關稅成本攀升而被迫重組,供應鏈面臨人為斷裂的風險。這種保護主義措施或許能在短期內保住若干工廠就業,但長期而言必將推高國內物價、抑制技術創新活力,最終損害消費者權益與企業競爭力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近期表示,美國對華關稅導致該國家庭年均支出增加約1300美元,而受保護產業的就業增長卻微乎其微。
在此背景下,香港的實踐經驗具有重要啟示意義。面對此變局,香港需要以更高水平的「開放」破解「泛安全化」困局。這座城市以實證表明:真正的經濟安全閥在於市場的靈活適應力與多元化佈局。特別當內地面對關稅衝擊,遭遇外貿訂單縮減、外資信心波動之際,香港更需以實際行動展現開放型經濟的獨特韌性。具體路徑包括:深度激活大灣區「一小時生活圈」的協同效應,將「一帶一路」的樞紐優勢轉化為實質性合作項目;在鞏固傳統歐美市場的同時,積極開拓東盟新興消費市場,並在中東能源轉型中尋找新機遇;透過「北部都會區」創科布局,打造貫穿基礎研究、成果轉化到產業應用的高增值產業鏈,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超級聯繫人的不可替代角色;始終堅守自由港「零關稅、零壁壘」的制度本色,以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匯聚全球精英。根據投資推廣署數據,2023年香港初創企業數量逆勢增長12%,外資企業地區總部數量保持穩定,印證這條路徑的可行性。
縱觀歷史長河,從大航海時代到WTO成立,保護主義的高牆無一例外終告傾頹。如今香港這座從不築牆的城市,應以「一國兩制」的獨特優勢,擔當連接東西方的戰略橋樑。通過構建更開放、更包容的國際經貿網絡,為動盪的全球經濟編織可靠的安全網。面對逆全球化暗流,香港這座百年商埠有能力也有責任向世界宣告:拆除人為藩籬、擁抱開放合作,才是維護經濟安全最堅實的防線。「在別人關門時,我們更要把窗開得更大」——這或許正是香港在變局中最明智的戰略選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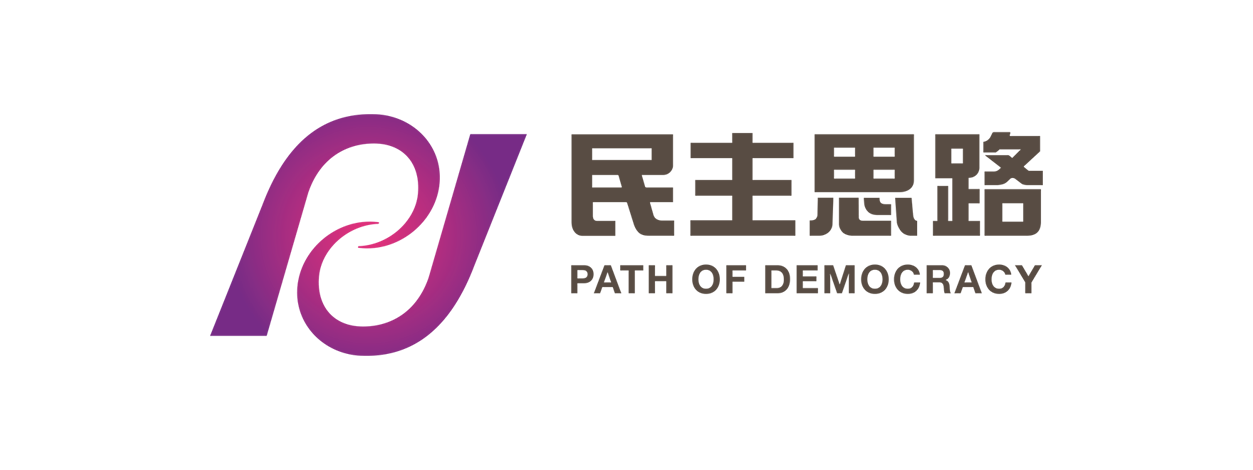
 EN
EN Login
Login Donation
Donation

 Back
Back